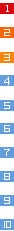谈艺六则
文/何光锐
艺术家为什么要读书?
1944年傅雷在给黄宾虹的信中叹道:“画家不读书,南北通病,言之可慨。”
现在回过头看,那个时代的不少画家倒是着实读了一些书的。如果傅雷活在今天,不知会作何感想?
艺术家的素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艺术家的知识结构不可能相同也不必相同。然而,起码的“底线”是不能没有的。
多年前的一个场景曾经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的决赛上,一位进入隶书前六名的选手,在综合素质比试中得了零分。其间当主持人问到“中国传统的‘五岳’是指哪五座山?”时,他居然张大着嘴巴,愣是一个也答不上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类似的尴尬,在比赛过程中比比皆是,一场电视大赛,无意中把许多书法家的“家底”给抖露了出来。
艺术家为什么要读书?从浅近处说起,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除了技艺才情的前提外,还要求创作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层次。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底蕴是区分艺术家和工匠的重要标准,而“营养不良”除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格调境界外,还容易在细节处捉襟见肘,露出“马脚”,贻笑大方。
露马脚与否还不是问题的关键。读书的真正意义并非为了掉书袋,做学究,而在于明理。“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所贵乎读书者,“济乎义”也,“贯乎道”也,而卒能“会其通”也。
对于艺术家来说,技艺的训练、素材的积累固然不可忽视,而哲理的通达、境界的提升和情趣的陶养却是头等大事。有人问周臣为何不及弟子唐寅,周臣回答说:“但少唐生三千卷书耳”。这虽然是谦逊之言,却也道出了实情。
孔子曰:君子不器。其实孔子没有反对君子掌握具体的才能,他老人家自己射箭驾车样样精通,还当过仓管员和饲养员,他之所以讲“不器”,只是为了强调与“器”相对应的更为重要的“道”。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记》里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白——“学技必先学文……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锁钥,锁钥维何?文理二字是也。寻常锁钥,止开一锁,一锁止管一门;而文理二字之锁钥,其所管者不止千门万户,盖合天上地下、万国九洲,其大至于无外,其小至于无内,一切当行当学之事,无不握其枢纽而司其出入者也……”天下万事既然都有开门的钥匙,那么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拿到这把“通用”的钥匙。所以,提倡读书看上去似乎是不切实际的“迂阔”之论,其实乃一条无法绕开的正途。
巴西是足球王国,巴西人有一个说法:“足球是上半身的运动”。这个“上半身”可谓意味深长:意识、灵感、意志、合作精神……这些与什么有关?还是文化。一项被认为最“粗鲁”的竞技运动尚且讲求修养,何况作为风雅之事的艺术?
艺术家不读书之所以成为“南北通病”,不外乎几种情况。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总有一些聪明绝顶的人,恃其私智,顾盼自雄,认为乖巧者无所不能,骨子里瞧不起读书这件事,瞧不起埋头读书的“笨伯”;“下愚”者,底子太差,无门可入,则视读书为畏途。除了这两种特殊情况外,大多数的艺术家们并非不想读书,只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们忙。如今艺术是个竞技场,尚未崭露头角的忙于“科举”,小试锋芒的忙于炒作经营,声名显赫的忙于立山头,树“流派”,或暗地角力,或互为声气,终日前呼后拥,应酬吹牛,“大丈夫不当如此乎?”。
但他们大都知道书本的好处,必要时还得摆摆空城计,弄弄玄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包装自己的作品,正如艺评家吴亮所言,“不会画和故意画得拙劣之间的区别,无非是有没有找到一个时髦的说法”。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多”,忙里出错,露出点马脚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艺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艺术鉴赏群体和氛围的缺失,快餐文化的泛滥,这些深层的社会环境因素,也让不读书的艺术家们得以从容周旋于其间。
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浮躁的现象存在,更何况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艺术已然成为一个饭碗。其实每个时代也都不乏沉潜笃定者,他们有的时候并不在公众的视野之内,但他们却是文化传承与延伸的脉络所系。
与傅雷同时代的画家溥心畬,一贯主张以读书为作画之根本,他曾对别人说:“如若你要称我为画家,不如称我为书家;如若称我为书家,不如称我为诗人;如若称我为诗人,更不如称我为学者。”
溥心畲终归还是以画名世,但他的这种认识与追求,却能给我们带来启发。
“靠谱”
在百度百科上搜索“靠谱”这两个字,得出的解释是——北方方言,后现代流行词汇,就是可靠、值得相信的意思。再搜了下“离谱”,指的是事物的发展脱离了规律性或公认的准则,不着调,不和谐。
以前人以为,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有个谱。比如弹琴有琴谱,下棋有棋谱,画画有竹谱、梅谱,《芥子园画传》就是顶有名的画谱。
问题是,如今琴棋都还有“谱”在,而公认最为高深莫测,动辄以“道”来标榜的的书画艺术,反而没有“谱”了。
我经常用“卡拉OK”来形容今天的书画艺术。“卡拉OK”的最大好处就是没有门槛,只要不是哑巴,拿起麦克风就可以引吭高歌。只要自我感觉良好,尽可以声情并茂,不须在意跑不跑调,也不用管别人是否受得了。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热衷于写写画画,一是可以附庸于风雅之列,二是“敢唱就会红”,既容易上手,也方便旁人鼓掌。
将艺术与竞技进行横向对照,是件颇有意思的事情。竞技体育的好处,在于有一套人人认可的鲜明的规则,规则之下,水平立现、胜负立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拳击打球赛跑举重不用说了,就连体操、花样滑冰这种表演性质的项目,你也得先达到一定的技术难度,然后进一步才能出风格比神采,如果连基本动作都掌握不了,就只有摔得满地找牙,当众出丑。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艺术只是用来陶冶性情的,或者援引西方人的说法,“艺术是一种‘非功利性、非竞争性’的‘自由’的游戏”。然而,“非竞争性”也给这一“游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优劣高下,只能通过会意于心的鉴赏,缺乏明确、公正、通行的评判标准。一旦较起真来,反而弄得说法纷纭,是非蜂起,鱼龙莫辨。
其实大凡能够成为一个专业,都得有个“谱”,有个门槛在。中国人却爱把事情弄得高妙玄乎,一提到艺术,就要讲“意境”论“气韵”。高妙玄乎本没有错,但那是最高阶段的事,而不应该是起始阶段的追求。书画艺术也确乎高妙,但今天的艺术家们似乎不愿意入“门”,都愿意直奔最高处而去。他们忘记了书画原本也是一个专业,也应该有个绕不过的“谱”在,遂使书画艺术成为最缺乏专业精神的一个领域。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书画“小道”,乃诗文之“余事”,那无疑更要以“余力”之“余力”来对付了。即便如此,我们的古人们在这些寄托情怀“小道”之上,仍然有着虔诚谨饬的“问道”之心,而并非含糊草率,敷衍了事。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这是诗人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的名句。为什么要“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工作效率如此之低?笔者以前对这一点也不是太理解,是不是古人故意把作画过程神秘化,过于矜持了?直到有一次翻读画史,看了一段关于吴镇的文字才恍然大悟。“元四家”之一吴镇画山水擅长以湿墨点苔,却“每积画盈筐,不轻点之”,语人曰:“今日意思昏钝,俟精明澄澈时为之也”。的确,人的情绪有变化,精神有起伏,并不是每个时候都适宜作画。在“意思昏钝”的状态下,连点苔都点不好,自然也画不好“一水”与“一石”。
这实际上是个态度问题。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这样表达他的态度:“……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终始,如戒严敌,然后毕。此岂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小大,例须如此,而后有成。”画一幅画,居然要戒慎从事,如临大敌,这说法听来似乎很有趣?据传,宋徽宗领导下的皇家画院,对于孔雀开屏是先举右脚还是左脚这样的细节都十分在意,这种较真的态度似乎有点“纠结”?然而,“天下之事,不论小大,例须如此,而后有成”,是矣!是矣!
今天大家都爱说,“态度决定一切”。对待书画艺术,古人的态度“如戒严敌”,今人的态度如“卡拉OK”。这就决定了古人能够在实践中梳理提炼出“画谱”,而今人的书画却大多不“靠谱”。
不如守约
这个守“约”,说的不是跟朋友约会的“约”,而是与“博”相对应的“约”。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守约是不容易做到的。跟前人相比,我们面对的信息太多,资料太多,诱惑太多。这本来是很幸福的事情,然而,要抵挡住诱惑,却需要觉悟和定力。
周围有不少搞书法的朋友,每年看他们的各种展览,总的感觉是大家都在竭力地想端出一些“新”的东西,前年整的是隋唐写经,去年是汉简,今年又从战国的兵器上搬了些古怪的篆书来。但他们的书法究竟搞成了没有呢?私下交流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仍旧透露出一丝茫然。
这时候很自然地会想起一句有名的话来——“真迹数行可名世”。
古人也有烦恼,他们的烦恼不是资料太多,而是太少。“真迹”是从事艺术的宝贵资源,谁占有了资源,哪怕只是廖廖“数行”,谁就离成功不远。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记载,钟繇向韦诞苦求蔡邕的笔法秘诀,韦诞不依,于是大闹三天,槌胸至呕血,还是曹操拿五灵丹救活了他。“欧阳询见索靖古碑,驻马观之。去数步复还,下马观之。倦则布毡坐观之,宿碑旁三日乃去。”欧阳询没有数码相机,只好在碑下睡了三个晚上。但钟繇和欧阳询的书法终归是搞成了。
记得有一年的高考作文题,要求根据一幅漫画写成议论文,漫画画的是连成一片的地下泉水,和未能伸及泉水的几口深浅不一的井。其实这个道理古人已经讲得很透澈,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里,转述了友人吴嘉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无论为学为文为艺,总以“深入”为第一要义,惟有深入方能尝到真滋味,获得真领悟,方能“掘井及泉”“探得骊珠还”。而“深入”的前提是专注与守约,正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那么,今人为什么总是显得“花心”,做不到沉潜执着、专注守约呢?资料太多,来得太容易是一个方面。南宋朱熹曾说:“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都有印本,多了。”处在网络时代的我们,比起朱熹时代的“今人”,面对的知识信息何止万倍?因而更需要克制贪多务得,急切冒进的心理。另一方面,“花心”的真正根源在于“名心”“利心”。还是用朱熹的一句话来说透:“……今来学者,(读书)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可见“花心”也不是今人的专利,只是今人更甚于古人。今天的书法家们,临帖练字一般是专要作展览用,一般是要写得“新奇”,生怕写得不如别人的好。问题是今年“新奇”,明年还得“新奇”,于是到处翻找那些生僻的材料,那些别人还没来得及“开发”的“资源”,从花样到花样,实际上艺术的“道行”并没有真正的变化,就如俗话说的“熊掰玉米棒子,一路掰一路丢”,最后落个两手空空。
我常对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少产生震撼人心的文学巨作?因为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爱情与乡愁,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淡化了情感根源。男女交往没有了限制,“爱情”随处可得,随时可以结束,“快餐化”的选择之下难以再有荡气回肠的碰撞。张艺谋为拍电影《山楂树》,在全国范围找不到“纯情的眼神”,虽有炒作嫌疑,但他的感叹也的确反映了某种事实。交通通信的极度发达,驱走了由地理隔阻造成的距离感,那种“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羁旅之思、乡关之慕也就不复存在。真正的乡愁,恐怕只有杨利伟在太空中回望那颗蓝色星球时,才能体会到吧。
艺术上的“纯情”,同样难以寻觅。专注守约,先得耐得住寂寞,而学问艺文,从来就是寂寞之道。
有几位或从福州走出,或仍留在福州的60多岁的篆刻家、书法家,都有着扎实深厚的功力。笔者在与他们的交往当中,发现他们年轻时都曾做过“脱影双钩”的工夫。那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对艺术的痴迷让他们心无旁骛,而艺术的资料则极其匮乏,有谁得到片纸只字,友朋间辗转相借,灯下勾摹,全神以赴,不知东方之既白。而正是这种“双钩”经历,让他们锤炼了手眼工夫,在艺术上尝到了真滋味,获得了真领悟,一生受益无穷。
其实资料信息只是“中性”的,如何对待和运用资料,则“存乎一心”。今天的我们,面对着古人未能梦见的丰富讯息和交流渠道,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击交汇,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这实际上是亘古未有之崭新机遇,从道理上说,应当有所因应,有所创造。然而,为什么放眼看去,只是一片喧嚣嘈杂、光怪陆离?
钱穆先生当年在论及学者之“病”时说,“千言万语,只是一病,其病即在只求表现,不肯先认真进入学问之门”“未曾入,急求出”“尽在门外大踏步乱跑,穷气竭力,也没有一归宿处”。此话移之于今天的艺术领域,恰能切中时弊。
挖井的目的是“及泉”,没有找到水之前老想换个地方挖,等于前功尽弃,殊不知底下的源泉是连成一片的,从哪里挖并不是最重要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你总得选择一条走到底。至于到了罗马以后做什么,那是后面的事情。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不如守约。
“笔软”的秘密
中国古典书论、画论以实践为基底,以体悟为秘钥,文中多有感性的比喻与描述,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悬针垂露”“奔雷坠石”之类,因此有人讥之为“一整套精致的‘形容词谱系’”。
然而,对于艺术领域的一些重要原理,古人虽未展开“学术论文”般逻辑严密的论证,却往往于只言片语间道破“天机”。此等处,不可以“文学性语言”等闲视之。
传为东汉蔡邕的书论《九势》中,有这样一句话——“笔软则奇怪生焉。”
这真是一句“奇怪”的话语。何谓“笔软”?何谓“奇怪”?何以“笔软”则“奇怪生焉”?针对它的真实含义,历来聚讼纷纷,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如果书写者笔力软弱,则书写过程中不能如意,笔下出现各种不合规范的丑怪线条和结构。第二种解释与之相反,认为因毛笔富于弹性的特点,如果书写者运用得法,就能产生变化多端、出人意表的精彩效果。
我们知道,释读古文,必须“原汤化原食”,把句子放到原文的整个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蔡邕的一段原话是这样的:“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行,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其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挡,势去不可遏,笔软则奇怪生焉。”细细咀嚼体会之后,就可以把第一种解释排除。因为文中连续出现的“自然”“阴阳”“藏头护尾”“肌肤之丽”“势来”“势去”等词语,环环相扣,都与毛笔富于弹性的特点,亦即“笔软”直接相关。惟“笔软”,方可“藏头护尾”,方有“肌肤之丽”,方能“形势出矣”“奇怪生焉”。
实际上,这段文字包含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一大奥秘。
世界各民族文字,在其肇端之际,多以契刻或硬物描画为主。中国人后来发明出毛笔,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毛笔产生后的几千年中,多少智者能人日日操弄使用,竟然没有推翻这位性格“柔软”的管城侯,以一种更便利的工具取代之。只要拿过毛笔的都知道,这支笔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多么地难以控制,笔毫一入纸,立即就失去“平衡”,不是太重就是太轻,快了不成慢了更不成,那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就象从未溜过冰的人被套上冰鞋推到了场地中央。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似乎专门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我们的先贤在原本相对硬朗的狼毫笔之外,又增添了更软更不易对付的羊毫笔,而且还要加长笔锋。在纸张的应用上也是如此,从表面光滑硬挺的熟纸,演进到柔软而易于渗化的生宣。他们的用意,无异于要“戴着镣铐跳舞”。而深究其中妙理,则可以明了为何只有中国发展出纯粹以文字书写为形式的书法艺术,以及中国画何以形成“笔墨中心论”。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曾经触及这一问题,他说:“中国之毛笔,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国的字体,学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却用最奇特不整的笔姿组合起来,而以千变万化的结构布置,留待书家自己去决定创造。”
注重表达内在节奏韵律,抒发情性,呈现哲理,是所有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取向。对于书法而言,正是这些“形而上”的需要,对工具材料提出了选择,这就是毛笔诞生的必然性所在。换句“玄虚”点的话说,惟具弹性之物方能“载道”。如若无法传递韵律,则无“流美”可言,更谈不上体现情性与哲理,谈不上“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了。因此,书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生命化的艺术,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毛笔的特殊性不容忽视。
“笔软则奇怪生焉”,蔡邕所用的“奇怪”一词,提示了书法线条在艺术表现上的丰富性——浓、淡、枯、润,粗、细、刚、柔,稳与险,畅与涩,老与嫩,张扬与蕴蓄,精微与浑茫,迅捷与雍容,雄壮与优雅,豪迈与谨严,洒脱与沉郁……任何一门艺术,都建立在对复杂多重矛盾关系的驾驭调和上,艺术的高度与艺术的难度紧密相关。仍然拿竞技体育来打个比方:足球为什么被公认为世界第一运动,让无数人如痴似狂?正是由于这项运动以人体中最为笨拙的部位,接触物体中最难以控制的球体,参加一种人数最多的集体角逐,因而最富起伏变化,最难以预测,最具偶然性和戏剧性。“脚拙”“球圆”“人多”,于是,“奇怪生焉”。
另外,由于毛笔的软而难操,让习书者不得不放下傲慢自我的心态,和逾级邋等的企图,静气澄怀、日复一日地在笔墨纸三者间周旋对话,熟悉、体认、顺应其性理,才有可能渐次向挥洒如意、心手相忘的“段位”靠拢。否则,即便有满肚子的才思,也只能感叹“眼中有神,腕下有鬼”了。在这个过程中,毛笔之“软”,实际上对躁急刚愎的人为之力,形成了一道阻挡、缓冲、化解的“沼泽地”。“笔力”提升之进阶,伴随着人对自然的尊重、认识与相融,此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要义。
“夫书肇于自然”,而其至高境界,乃达于自然。
古是什么?
书法要回归“二王”,绘画要直溯宋元,在艺术领域,许多人开始探究“古法”,追寻“古意”,一种崇古,乃至“复古”的风气,出现已久。与此同时,不同的声音,对“古”的质疑和抨击,也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我们身处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崛起,国人的文化自觉正在苏醒。一百多年前所谓的文化碰撞,其实质是在自卑心理下的自我否定、“全线溃退”与“去传统化”,而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碰撞来日方长。在这样一个众流交汇、视角多元、话语权争夺激烈的当口,围绕“古”的讨论,成为了一个前沿的话题,如何理解“古”、对待“古”,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
那么,“古”,究竟是什么?
“古”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古”不是“昔”,不是“旧”。凡是“旧”的东西都一律曾经“新”过,但它是速朽的,被淘汰的。现代风格的家私可能很快过时,然而,我们看看明式家具,那种简约静穆之美,至今仍不断地给全世界的设计师们带来创作的灵感。
“古”也不是某些具体的形式。陈丹青在他的《退步集续篇》中说得很好:“……文艺复兴绘画的种种造型散韵似乎早已预告了现代意大利皮鞋与男装,俊秀雅逸……”皮鞋跟绘画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你会发现,由文艺复兴大美学滋养陶冶的民族,于造型之美何其干练而精明……”
实际上,关于“古”的种种误解,都是将“古” 作了实体化的理解,犹如刻舟求剑,企图到前人遗迹和故纸堆中搜罗印证,把“古”当成既定、僵化、封闭的东西,进而要么一味摹古,泥古不化,要么竭力谤古,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古”。
有人考证出,东晋人写字的姿势是席地而坐、执卷而书,为了书写流利,必须用手指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所谓的“古法”就是转笔的技巧和方法。问题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桌子椅子,怎么办?还要不要这个“古法”?笔者常和一些书法家朋友讨论,我们应该怎样学习王羲之?是仅仅模仿他的用笔结体,还是学习他的境界识度、传承态度和创新精神?假设生宣和羊毫在东晋时就发明了,王羲之会如何对付,是否会写出另一种风味的书法?
齐白石说,“……其篆刻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越千古……”。齐白石没有执着于古人的样式,他学习的是古人的“不蠢”。如今齐白石也成了古人,那么,“古”安在哉?在乎秦砖汉瓦?在乎拍卖场上的齐氏篆刻?
“古”是活泼的,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古”是超越于时空与形式之上的,是传统中合理的、优秀的成分。“古”是文化的精神内核,是“道”之所存。
“古”和“新”并非对立,真正的“古”总是常变常新的,真正的“新”总是暗合于古的。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革新运动,都以“复古”为号召。窃以为,“复古”之“复”,不是“重复”,走回头路,而应理解为“回复”,从偏途回到正道上来。
提倡复古,开一代风气的赵孟頫,主张“画贵有古意”,其实主要是纠正南宋以来柔媚纤巧和刚猛率易两种不良倾向,强调“中和之美”。在其启发引领下,元代山水画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
韩愈发起唐代古文运动,他的名言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他的“复古”并没有袭取前人语调,而是“戛戛独造”“唯陈言之务去”,恢复古代散文清新简练之传统,一扫南北朝以来矫揉造作之时弊。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曰:“李唐群英,惟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如此看来,韩愈的文章,究竟是“古”还是“新”?
值得注意的,还有苏轼评价韩愈的两句话——“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有衰靡,有偏溺,而后有复古。
入古出新,借古开今,乃是一种因果关系。按照“现代化”学的新观点,“现代”与“传统’不能截然分立,“现代”只能从“传统”中逐渐生出。
德国文化哲学家蓝德曼说:“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对于书画等中国传统艺术来说,真正的困境在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今天的我们已经失去,甚至不再认识这个“高度”了。
充分进入传统,重新认识传统,把握传统的内在精神,当下的“复古”潮流若能以此为取向,则前景或许未可限量。
当然,重要的,是“不蠢”。
中国绘画中“远意”的实现
经常有人问我,当代中国画的水平与古人相比如何,我只好答曰:不好说,说不来。
水平这东西真不容易说清楚。你说笔墨,他说技法只是为表达思想服务;你说境界,他说我们境界也很高,视野比古人开阔多了。
但是,如果问我当代绘画跟古代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会很肯定地回答,有。最大的不同在于,古人的绘画,常常能表现出一种“远意”,甚至可以说,这种“远意”是中国传统绘画到了成熟阶段之后最深层次的追求。你哪怕随意找来一张佚名的古代山水画,都能体会到画面中“远意”的存在。而今天的中国画,尽管风格门类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却惟独缺席了能够表达“远意”的作者和作品。
那么,中国的绘画为什么要表达“远意”呢?
这个问题比较大,要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天地宇宙的看法说起。
一部《庄子》,开篇就是《逍遥游》。所谓“逍遥游”,就是试图摆脱生命中的束缚与障碍,“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无所依傍地到达理想中的“远方”,借此比喻精神上的的绝对自由。
然而,在俗世中浮沉的人们,“自由”谈何容易?对“自由”的响慕,往往正是对付现实压迫的一种心理平衡。魏晋人最崇尚自由放浪的生活态度,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环境最为酷烈,只有纵情山水、享乐与玄谈,才能“暂得于己”,让惨淡压抑的人生透出一丝缝隙来。中国人所特有的的山水诗、山水画都于此际肇端,隐逸思想也于此际发达。
当一个人流连于山水丘壑时,可以“远”于俗情,得到精神上的解放。这是中国人逃避现实的独特方式,也是山水画能够在中国绘画中成为独立且最为重要的画科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妨来细读一下晋人嵇康有名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兰圃、华山、平皋、长川,无非丘壑山水;息徒、秣马、流磻、垂纶,无非解脱放下。把这些场景组织起来,无非一幅幅山水画。而描绘这些山水画面意欲何为呢?重要的是后面几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飞鸿”象征的正是一种“远意”,而这“远意”最终又指向“游心太玄”的自在自得。
对远意的追寻,成为中国文人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唐人贾岛曰:“分首芳草时,远意青天外。”元人熊鉌曰:“我来武夷山,远意超千古。”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曰:“春山无近远,远意一为林。未少云飞处,何来人世心?”
以个体之生命,突破世间之束缚,体验天地宇宙之永恒,体味人在此中之自由,山水诗、山水画从这个角度承载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邃寄托。
绘画既能寄托“远意”,接下来问题来了:这种高渺玄虚的“远意”如何在一幅具体的画面上得以实现?
以“卧游”之说闻名的晋宋间画家宗炳,撰写了号称中国第一篇山水画论的《画山水序》,内中云:“坚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千仞之高、百里之迥,是画家想要表现的“远意”,那么手法是什么呢?宗炳讲得非常含糊笼统……坚划三寸、横墨数尺,单凭这八个字就可以做到了。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理论先行”。根据唐代张彦远对六朝绘画的描述,当时的山水画作为人物画的附庸,仍处于稚拙状态:“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怎能表现出“百里之迥”的“远意”呢?张氏又言:“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虽说山水画独立、成熟于隋唐,但是从吴道子到李思训、李昭道,包括标榜“枕上见千里”的王维,都没有完全解决关于“远”的问题,直到郭熙的出现。
北宋郭思纂集《林泉高致》,记载其父郭熙提出的理论:“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现代人自作聪明,往往把郭熙的“三远”作为中国人的透视观,来“对抗”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实际上,这既是对郭熙的误解,又是对自身绘画传统的菲薄。郭熙提出“远”的观念,目的并不在于忠实地“拷贝”自然,而是为了通过恰当的图式,突破山水在形质上的局限。“远”是山水从实在的形质到虚灵的想象的延伸,近处的山川树石,衬托出远处无尽的虚空,这虚空恰是“道”之所存,宇宙之本质、天地之化机所在。魏晋人所追求的精神自由,终于被安顿在那一抹浅黛色的“远意”之中了。
然而,这样一幅山水画被创作出来,作为观者,可以从中体悟到“远意”所带来的心灵上的抚慰,而对于创作者来说,却是一项严谨而耗费精力的“工程”,因为空间感的呈现,无疑是绘画当中有着相当难度的技术活。据郭思回忆,郭熙创作时态度极为认真,每作一图,必酝酿再三,苦心经营,“如戒严敌”“如迓大宾”“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岂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
撇开为稻粱谋的画匠不论,对于本想通过画画来“解脱放下”文人们来说,“如戒严敌”的创作岂非南辕北辙,与“远意”相悖?于是,有胆有识的文人领袖苏轼带头站了出来,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一句是“君子可寓意于物,但不可留意于物”,另一句是“:“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这两句名言可以视为此后波澜壮阔的文人画潮流的思想总纲领。
既然画画的本意是“畅神”与“怡情”,那么,一段枯木、一片怪石同样可以寄托“远意”。而观赏评价“士人画”的标准是“如阅天下马”,关键之处在于“意气俊发”,“意”在远则远,皮毛形似反而成为令画者与观者倦怠的羁绊。
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意气俊发”如何在一张“士人画”上得以体现?毫无疑问,只有采取书法性用笔,让原本作为绘画手段的“笔墨”成为绘画的主体,才能达到抒情写意的自由。于是,宋人苏轼的“理论先行”,再次通过一整代元人的绘画实践得到印证。倪云林说:“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这让我们想起了嵇康那首诗中的另外两句——“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如此看来,中国绘画中“远意”的实现,经历了由题材到图式再到笔墨,由移情自然到观照自然再到体悟心性,由向外探求转而向内修为的发展路线。
现在,不妨把话题再回到文章的开头,为什么当代的中国画普遍地缺乏“远意”?
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代画家中的大多数都还在沉酣于角逐名利。他们并没有感受到俗世的压迫,相反都觉得“赶上了好日子”,一个个“意气俊发”忙着“抢钱”和“数钱”,并没有闲心来关注什么“远意”。即便有个别聪明之辈悟到了“远意”的好处,也只会把“远意”用于包装,以利于更好地“抢钱”。
何光锐,福建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艺术评论家。
| 


972aa3a2-11e9-4f4b-8c48-819c24e2af0c.jpg)
a577495c-6013-44d1-b8c8-431cba4a1b09.jpg)

07fd1243-7b66-48a4-9066-0735a8044eca.jpg)
0caed035-ee2a-4176-85d7-9123fed053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