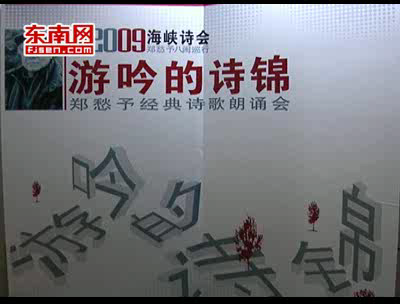郑杭生:好的。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问题,我已经谈过了一些。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耳顺”之年,我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点想法。我主要想谈这样两点:一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二是中国社会在当前还需要做些什么。
第一,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去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人们多数都高度评价后三十年,这是对的,还有就是国内外有一种思潮把前三十年说的一无是处。因此我写文章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一些成果,其为后三十年实质上打下了许多方面的基础:如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像原来总得听从外国人的指挥;又如,工业化基础的建立,特别是我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功拥有了核力量,这保证了我国有自我防卫的能力等等。我还着重指出了国际上的一种比较研究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国当前社会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核心的观点: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又走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什么转折呢?就是我们国家再要发展,必须要调整发展方式,要实现从初级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变。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我们以往的发展模式,我们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主要是脱贫和达到小康;发展手段是初级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发展资源是初级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等;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错位现象;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我们还存在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许多“类发展困境”。应当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大国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当我们发展到当前这样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发展道路有所反思,有所提升,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开始寻找走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必须树立起科学发展观,走一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人为本的道路。我曾经在几个场合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调适能力极强的社会。我相信,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来自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童 潇:郑老,我不知我的概括是否正确。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至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以严复、以孙本文、晏阳初、梁漱溟和吴文藻等为代表,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开启了对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并承担了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创造条件;第二代学人则以费孝通、雷洁琼等为代表,他们则开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部分学者还概括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而第三代学者则以您、陆学艺、邓伟志、吴铎等诸位教授为代表。这三代学人都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整体来看,我国社会学界欣欣向荣。您在《中国社会学三十年》这本书中谈到,中国社会学要进一步处理好“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这五对关系,能否借此机会,请您再从社会学发展趋势的角度,谈一谈您对社会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学要进一步取得进步的相关看法?
- 2009-10-21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
|